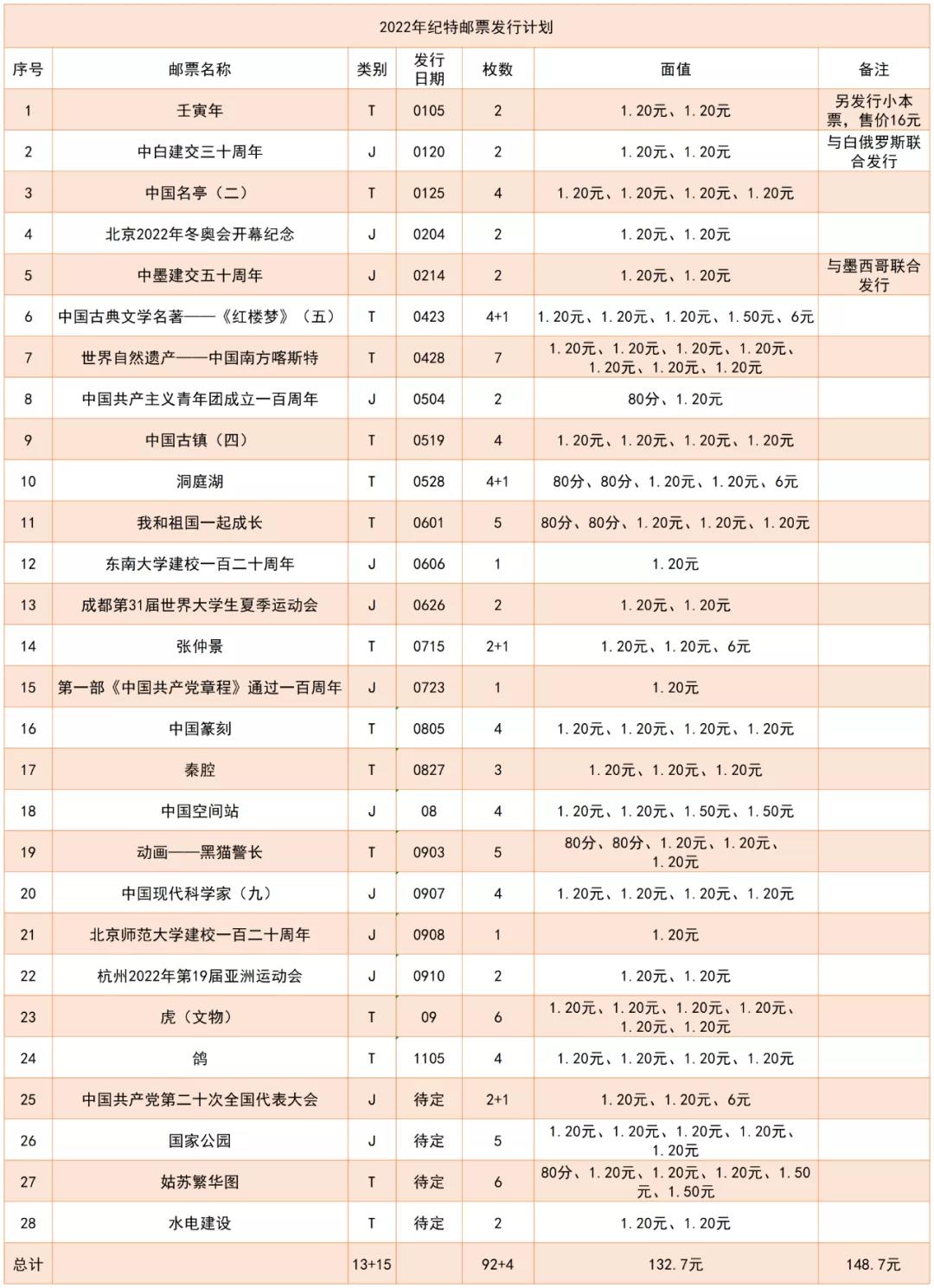原标题:文化周刊丨大地岁时:造访
傅菲
 (资料图)
(资料图)
山坞在针叶林后面。针叶林呈梯级,往山巅延伸。我站在窗口,就可以清晰地看见这片森林。偶有突兀而出的高大杉树,如一股不散的炊烟。春末夏初,森林在大多时候被淡雾所笼罩,或被雨遮蔽,只露出一个山尖。在闲日,我无处溜达时,便去林缘地带观鸟或采集野花。
一条机耕道通往森林。机耕道是黄土路,进山的拖拉机磨出坑坑洼洼和路脊。有时,拖拉机陷在坑洞,突突突,冒出滚滚黑烟,油门轰了十几分钟后熄火了。在年初,有人拉来炮渣铺路,请压路机压实。炮渣路渗水,即使是雨天,走起来也很清爽。我便每日中午去那片山野。机耕道一直弯向山脚下的枫香林。一日,我发现在岔路口有一条巴掌宽的小路,藏在苦竹林。苦竹密密匝匝,笋也密密匝匝。小路被苦竹弯垂的树梢密闭了。我只得弓着腰钻了进去。
小路沿着林缘往北,有两百余米长。走出苦竹林,豁然开朗。这是一个被山峦挡住了外界视线的山坞,坡上的阔叶林给人原始、神秘之感。山坞朝东,有一块约有三亩大的荒地,在早年被人种上了数十株桃树和梨树。我的到访显得意外和突然,桃花梨花忍不住在枝头颤动。细腰蜂嗡嗡嗡。山野沉寂,嗡嗡声显得有些震耳欲聋。一树红艳一树白艳,花粉团簇。山坞收紧之处,是一块水塘。水塘半干涸,水积在塘底,呈锅状。鲫鱼和白鲦,乌黑黑地拥挤在一起,拱起淤青色的鱼脊背。我扔一个小石块下去,鱼激烈地跳起来,甩着尾巴,溅起水花,瞬间又聚集在一起。鱼在等待雨,灌满水塘。但雨季迟迟没有来,前些日的几场酥雨,并没有带来丰沛的水量,只是淋湿了塘边的淤泥。之前,淤泥是皲裂的,有了水,泥皮溃疡一样烂开。大蓟和紫云英从淤泥里长了出来,零零星星。紫云英有了小骨朵,油灯一样亮了起来。
水塘之北的山边,有一栋民房。民房只有一层,盖瓦,门锁紧闭。房前有一块半亩大的院子,方方正正。院子里有水池,可洗衣洗菜,晾衣杆架在两根竹桩上,已成了麻黑色。院子的地面并没有硬化,而是土夯,长出了稀稀的青苔。屋角的两边,各摆了八个土钵,种了许多花,有的植株已经彻底枯死,有的植株葱葱茏茏。丹顶红、草本海棠、姜花、菖蒲,再次从春天出发,茎叶繁茂。这些山野之物,熏染了春日之气。
这是一栋废弃的民房。看起来,房子在十余年前建起来,房墙的白色涂料还没改变颜色。是谁在这个山坞建房呢?当然,这是一个开阔、向阳的好地方。建房的人为什么又离开了呢?从山涧引来的泉水,依然注入四方形的水池,嘟嘟嘟。是水入池的声音,也是时间之声。我从屋檐下找了一把锄头,挖了野山茶、刚竹、木本绣球、赤楠,栽在植株死了的土钵,盖实了土浇透了水。那个离开房子的人,假如有一天回来,看到我种下的植物,活了下来,该是一件多么欣喜的事。
院子与水塘之间,是一个陡峭的土坡。土坡长着茂密的阔叶林,有多穗青冈栎、苦槠、山矾、大叶冬青等。树并不粗壮,却有十余米之高。苦槠正在幼发嫩叶,叶淡青微白,像罩着一团白雾。
那个曾打算在山坞生活或长居的人,在山涧入山坞的低洼处,还用石头砌了一个圆形的泄水池。池有十余平方米,深约两米。池底有一层白白的细沙,也许是被水带下来的。石壁上,裹了一层青苔。看起来,水池更像一口活水井。池中有几条点纹银鮈在游,许多小虾附着在青苔上。一棵桃树的树冠盖住了池口。倒映在池中的桃树,一下子生动了起来。飘落的桃花浮在水面上,与白云织在一起。云成了桃花云,缥缈于水云间。
在山坞闲走了半个下午,也没看到一个人来。桃花梨花兀自开,也兀自落。我很想认识那个种桃树梨树的人,认识那个建房修池的人。他为什么来到这里,为什么又离开。我觉得那个人,就是另一个我。
对生活,对生命,我有很多困惑。我尝试了很多方式去解答,都找不到令自己信服的答案。去山中访问,是我最喜欢的一种方式。而我每每去了山中回来,又冒出别的疑问。我又得不得更多次数去访问。在访问时,我目睹了四季的变化,物候的更替,内心获得了极大的纾解,我就可以乐观地活下去了。(傅菲)
关键词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