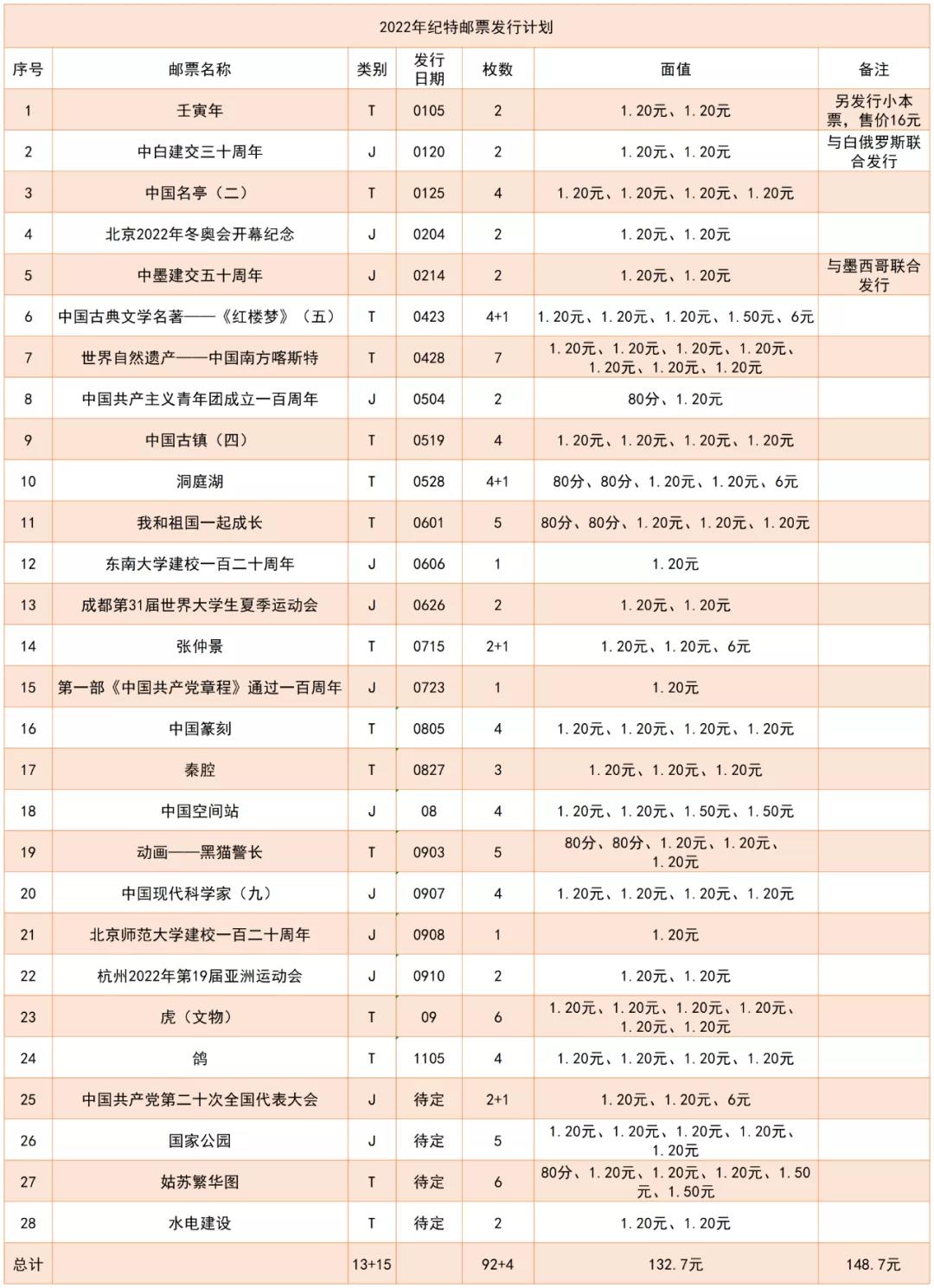刀锋未冷,江湖犹在。那个艺名中带“刀”的男人,如同任我行一样卷土重来。有人说,他此行是为杀上黑木崖,以报“被囚西湖牢底之仇”;也有人说,他仅仅是想向世人宣示,升级版的“吸星大法”威力几何。面对纷纷流言,他仍然保持一贯的沉默。但这沉默,却让我拾起一些童年时代的记忆碎片——
 (资料图片)
(资料图片)
在我的“70后”父亲的漫长务工生涯中,刀郎的歌,是绝对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。刀郎对于他的意义,或许只有金庸对于我爷爷的意义才堪比拟。
即使在他的同龄人中,我也从未见过像他那样喜欢刀郎的人,这甚至一度令我心生嫉妒。时隔十多年,我仍然记得,他一手提着在工厂举办的歌唱比赛中赢得的热水瓶,一手握着玉米棒子当话筒高唱刀郎的歌漫步回家的情形。那助他赢得热水瓶的参赛曲目,不用说也是刀郎的歌,尽管我已记不清楚了。
时至今日,我当然难以考证,刀郎的突然消失对于我父亲意味着什么。假如我问他,他一定会满脸问号,对此表示难以理解——一个远在天边的流行歌手的退隐,怎么会对一个困于生活的中年男人造成影响?
对于他的可能回答,我丝毫不会怀疑里面掺杂有半点矫情。如他一样,在城市之间疲于奔命的农民工们,大概不会对追星产生任何兴趣。包括音乐在内的一切艺术,对他们而言都是奢侈而纯粹的——喜欢一首歌却不必追捧其歌手,喜欢一首诗却不必崇拜其作者。这种审美品质,在这年头已然罕见。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作为歌手的刀郎,本就是为像我父亲一样的市井百姓而生的。他的歌词与音乐,不需要学院派苛求的精致含蓄与条条框框。一个忙碌终日的市场摊贩,一个筋疲力尽的建筑工人,只要能在深夜回家的路上,从那苍凉壮阔的词曲中获得一时快意,刀郎的作品也就足以登上大雅之堂。
事实上,在文学艺术领域,通俗与高雅本就没有明确的界限,尽管无数学者曾为此争执不休。每当想起大学时代,在文学课上发生的那些关于通俗文学与纯文学的争论,我都会感到一丝羞愧与遗憾。那时候,我还不太明白求知与求胜的区别,以至于苏格拉底式的思辨往往演变为智者学派式的争辩。
如今想来,一部文学史或艺术史,其实就是“民间派”与“学院派”彼此对立又相互融合的循环过程。以中国古典文学为例:浮华绮丽的六朝诗歌在宫廷宴会上走到尽头,雄浑开阔的盛唐诗歌便在江湖草泽间重获新生;萎靡不振的晚唐诗歌被士大夫们彻底玩坏,烟火撩人的宋元词曲便在勾栏酒肆悄然兴起……
不知你是否留意到,在电影《长安三万里》中出现的48首诗歌,有两首的作者是来自民间的无名氏——哥舒翰念诵的《哥舒歌》和裴十二念诵的《题玉泉溪》。在名诗人扎堆的时代背景中,编剧特意选出这两首格调明快的民间诗歌,或许便是一种暗示——唐诗的兴盛,正是基于生机勃勃的民间审美力量。
这种民间审美力量,既体现在李白的诗中,也体现在刀郎的歌中。关于这一点最好的说明,或许便是多年前我的一次亲身体验——
那天傍晚,我在一条西北沙漠公路上等到一辆大巴。车显然已行驶很久,乘客们疲惫不堪。突然间,车厢里的公放音乐切换到《西海情歌》,所有人似乎顿时充满了生命元气。开始是一个人唱,后来则是众人合唱;开始是浅吟低唱,后来则是引吭高唱。到最后,连司机也加入了这场欢乐颂……
对于刀郎来说,这一幕合唱抵得过一万句来自乐坛的赞誉。而在艺术面前,十多年前的那些乐坛恩怨也就显得无聊至极。同样感到无聊的,或许还有我的父亲。他不在乎那些名人是非,他在乎的是刀郎的新歌。遗憾的是,他听不懂。不过没关系,在他的手机里,还珍藏着那一首首百听不厌的老歌。
谢杨柳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关键词: